的确,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更缺乏自制力,更容易沉迷网络,而他们又处于接受教育期,肩负着全家的希望。如果因沉迷网络而影响了学习成绩,这不仅对其个人,而且对全家无疑是个重大危机,因此一些为此而焦灼的家长急于寻求解决之道。市场的嗅觉是灵敏的,一些人似乎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近年来众多鱼龙混杂的戒网瘾学校纷纷出笼。那些家有“网瘾少年”的家长与商家迅速达成“阳谋”,而那些网瘾少年则不由自主地成为“患者”,被送往戒网瘾学校“矫正”“治疗”。
有多少进入戒网瘾学校的少年成功戒除了网瘾,目前未见媒体报道,不得而知。然而媒体却披露了很多网瘾少年在戒网瘾学校遭受严重身心虐待的事例,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事例文中均有提及。
网瘾是不是一种病,即使是一种精神疾病,是否需要进行治疗和干预,如何进行治疗和干预,目前在国内外医学界并无定论,而官方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也并未明确将网瘾列为精神疾病。专业问题需要专业判断,在此我们暂且避开专业问题不谈。仅从法律上来审视,目前的网瘾治疗行为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制度缺失。一是谁才有资质对网瘾进行治疗。医疗机构和学校都是公益部门,涉及公民的身心健康和素质培养,必须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但现实中,无论作为网瘾的临床治疗机构,还是作为矫治网瘾行为的学校,其设立似乎都无门槛要求,或者说有这样的要求而形同虚设。二是网瘾治疗的程序问题。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即对依法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可以实行强制医疗,但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提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并由后者移送人民法院审理决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对法院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被强制医疗的人还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从强制医疗的程序机制可以看出法律对利益相关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严格保护。然而对于网瘾治疗,我们却没有看到相关的程序保护机制。须知,身染网瘾者没有且不可能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但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却遭到严重忽视。
在网瘾治疗过程中造成当事人伤亡毕竟是比较极端的事例,并不经常发生。据有过网瘾治疗经历的人反映,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其实并不仅仅是身心的,更多是自由的被剥夺和尊严的被漠视,而这一切竟然是在“爱”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更使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伤痛。在此引用知乎上一位网友的话,也许可以形容此种心情:
“从小到大,最害怕别人以爱之名为你做任何事情。没办法。从小到大,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生致力于研究精神病(或疯癫)的文化意义,他指出,所谓疯癫不过是自命理性的主流社会对非主流(非理性)的压制,监狱、学校、医院、军队、工厂等等就是这种压迫和规训的机构。医生同病人、教师同学生、军官与士兵、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如同法官与犯人的关系,近现代社会规范化权力和知识就是在这些关系中形成并运作的。依福柯的理论,对于网瘾现象及其所谓的治疗也可作如是观。(沈海平)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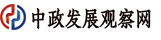 | 互联网频道
| 互联网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