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敬年近日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

▲1945年冬,杨敬年于英国。

▲2006年,杨敬年98岁,学生杨雁征摄于南开校园。
●现在,108岁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还是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1908年,或者叫“光绪三十四年”,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37岁留学、86岁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最新的作品是不久前口述完成的一篇长文,以读者和译者的身份,回忆自己与今年119岁的商务印书馆之间长达90余年的往来
●“能受天磨真铁汉”,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这辈子,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不是通过高举拳头,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将苦难咀嚼
●“你在任何时间见到一朵花,那都是同一朵花。”当我们遗憾没能早几年、在他精力更充沛时造访,杨敬年年轻的朋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现在,你会看到花盛开时看不到的、更耐人琢磨的地方”
108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安静地坐在沙发里,半合着双眼。黄斑性病变已在七八年间逐步偷走他的视力,105岁时的一场肺炎更彻底搅乱了他的时间表——此前,他一直在每天凌晨3点醒来,投入一整天的读书、工作。如今,这些都变得过于困难。
86岁,杨敬年从南开大学的讲台上退休;88岁,他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了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6年中连印16次,成为学术畅销书;95岁,他重新修订这部译著,增译6万字;到100岁时,他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人性谈》再版,他“在头脑里头修正”,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他最新的作品是不久前口述完成的一篇长文,以读者和译者的身份,回忆自己与今年119岁的商务印书馆之间长达90余年的往来。
现在,杨敬年安静地陷在沙发里,像本历史书,也像一本有关人生的哲学书。他已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行走,但还能信手拈来四书五经、李白杜甫的句子,随口背出朋友的手机号码,说起英文也还像在牛津大学时一样漂亮。他已不能自行读书看报,但还每天请保姆为自己念书,上下午各半小时到一小时。他的听力还很好,但在谈话中,不时要抬起一手,捂住一只耳朵,阻止声音刚从这边耳朵进来,就从那边出去。他已很难支撑长时间对话,在沙发上坐了半小时,便开始一点点地向一侧歪倒,但每个与他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感受到生命非凡的力量。
“你在任何时间见到一朵花,那都是同一朵花。”当我们遗憾没能早几年、在他精力更充沛时造访,杨敬年年轻的朋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现在,你会看到花盛开时看不到的、更耐人琢磨的地方。”
“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37岁留学、86岁退休、90岁翻译大部头……您对年龄增长的感知与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不怕。”
“支撑您的是什么?”
“追求学问。”
1908年,或者叫“光绪三十四年”,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在他出生一周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杨敬年说。
作为学者,那是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人类以往几代人的遭遇都被紧凑压缩进一代人的命运。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种种翻天覆地的变迁……对于一个家境贫寒、只能找免费学校读,又“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的年轻人,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
1927年,19岁的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数月后,“马日事变”,国民党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正醉心于共产主义、准备加入共青团的杨敬年愤而离校。
在贫困中为生计奔走数年,1932年,为免费读书,他考上国民党培养县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民政厅,杨敬年没去。“只有我一个人没去,我的同学都是高官厚禄,我穷啊,有人劝我何必这样呢,这么穷还读什么书?我没有听。”
1936年,28岁的杨敬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的两位——何廉、方显廷的得意门生。他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入学不足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跟着老师们在国民政府工作了七年,直做到财政部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
恩师何廉劝他放弃留学,“敬年,你年纪大了,劝你不必考留学了。如果你想搞银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如果你想搞政治,我介绍你给陈辞修。”但他既不想搞银行,也无意搞政治。
1945年,已经37岁的杨敬年从孟买坐上去伦敦的轮船,他考取第八期庚款留英,成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PE)专业的新生。
六十年后,当杨敬年的学生孟宪刚想要写写自己的老师,他发觉人们对杨敬年的关注多聚焦于他跟命运的搏斗,忽视了作为学者,他一生为求知和自我完善所付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这是他‘夕阳红’的真正原因和内容所在,是他的‘大故事’”。
那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聪明才智。”杨敬年说。
他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即使危及生命、牺牲快乐也在所不惜。人类的进化就在于这种追求,它没有止境,“总会有些什么东西,值得为它活着。”
现在,他仍很怀念牛津时代精力旺盛、只需专心治学的日子,用“无忧无虑”和“最幸福”形容那段时光。“我们每人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读书室。早晨,一个老头进来‘Good morning,Sir’,叫你起床,上午有女工给你整理被子、打扫房间。晚上,老头又来了,‘Good evening,Sir’,看你在不在房间。睡觉时,他来给你打开被子,‘Good night,Sir’。”
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研究政府分权问题的论文被认为“对知识有原创性的贡献并适于出版”。10月,放弃去美国工作的机会,他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邀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何廉很快远赴美国,临走前给杨敬年留了点金子,“敬年,你还年轻”。
护照就在手中,杨敬年可以说走就走,但他却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杨敬年40岁。
“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您说能从逆境中挺过来是因为有自己的原则?”
“对,以义制命。就是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就还是做。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读冯友兰的哲学,冯友兰说‘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作其所应作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
1949年,杨敬年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他为此忙了一两年,招兵买马、安排课程,与中央财政部订立合同共同办学。
因为“想多搞点科研工作”,1951年,他主动请辞系主任职务,准备收好师生们赠予的“财政系开拓者”锦旗潜心学术。
那时,他的牛津博士学位已一钱不值,他说那就“重新来过”,自学起俄文,翻译了三部苏联学术著作。
但紧接着,1957年,49岁的杨敬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专政对象”……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自此卧床。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离世。到1979年,杨敬年获得平反、重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他已经71岁。
“能受天磨真铁汉”,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这辈子,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不是通过高举拳头,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将苦难咀嚼。
“文革”中,有小朋友曾拦住他的路,问:“你是牛鬼蛇神吗?”杨敬年说,“是的”。又有小朋友问:“你今天当坏蛋了吗?”“当了。”“你明天还去做牛鬼蛇神吗?”“还要去的。”
也曾有悲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摇摆,他说那感觉像独行于沙漠,面前不外两条路:要死还是活。他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觉得这么死“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他靠毛泽东的话恢复心理平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他把眼前的遭遇也当成一场大慢性病。他看到一幅苏联画作上巨石在海潮中岿然不动,想“我就是这岩石,我要做这岩石”。他甚至觉得这二十多年的苦难对自己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我就觉得,党和人民,将来会给我一个公道。我也不管了,就拼命工作。”提起过往,108岁的杨敬年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读书是公费,劳动人民出钱培养的我,我总得做点工作报答他们。”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合200余万字,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地面震动时,杨敬年守在已瘫痪的妻子旁边,“我心里非常安定,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不能走。要死,那就同死呗。”地震后,他们搬进地震棚,众人惶惶的夜里,杨敬年独自搬着凳子,坐到大树底下,借星月照明,继续翻译他的书。
学生张俊山记得,“文革”后,杨敬年自告奋勇为经济系77级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结课时,他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 not by its force, 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这是一种信念。
“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
“俯仰无愧。”
“没有遗憾?”
“没有,我觉得我对得起所有的人,对得起国家,对吧?”
“对于人生,您有什么感悟愿与我们分享?”
“我小时候读过陈独秀的一部书,《独秀文存》。里面有四句话: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求生存、求发展。为了生存发展,一要求知,二要创造。”
平反后,年过七十的杨敬年决定要再工作20年。
他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从70岁讲到86岁退休;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编写教材、撰写专著、培养硕士生,把这门课程引入中国。他出版《人性谈》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的原因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认为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
1983年,我国首招博士研究生,75岁的杨敬年因超龄没有评上。到1994年退休,他共培养硕士生20名。
杨敬年说,跟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几十部专著,发表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他真是自惭形秽,“然而我却是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了”。
总有人为他鸣不平,但他觉得“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1998年,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关永强听了杨敬年的一场讲座。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小时中90岁的杨敬年始终站着,“这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尊重”。2004年,为了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关永强多次拜访杨敬年,“每一回,他都送我们到楼梯口,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走下去。那时他都96岁了,而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宋伟说自己是“杨老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杨敬年为他们译过书、写过导读。商务印书馆出版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写序,“杨老为我们请到了陈宗胜老师,陈老师做过南开经研所所长,也是天津市副秘书长,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法约到这样的专家的,这让我们非常感动,杨老师总是特别为别人着想。”
对于这些,杨敬年的“老门生”们早有感触。南开77级经济系的学生曾在一起交流,许多人都觉得杨敬年对自己十分照顾。“如果大家都这么感觉,那么杨先生为我们大家曾经是怎样的付出就一目了然了。”学生李忱说。
“杨先生是我毕生的老师”,在美国的邹玲至今每周都要给杨敬年打电话。38年前,因为跟不上专业英语进度,她到杨敬年家中辞课,惊讶地发现自己70岁的老师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难道你会输给我这70岁的老人吗?”杨敬年问,“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我家,我会给你解答。”
“杨先生70多岁学高等数学时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我说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超过它”。杨敬年的自画像是: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冯友兰在《新事论》里说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是因为有两个特点:一是把道德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一是满不在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108岁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还是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几个月前,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刚颁给他一个荣誉院士的称号,以表彰其终生对学术的贡献。
而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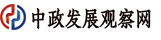 | 文化频道
| 文化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