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国际法委员会曾经解释,“历史水域”是基于历史而来,但要建立如此的权利,必须有严格的历史依据。中国在南海的历史依据,基于几个世纪的渊源。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设置珠崖﹑詹耳两郡,开始管理南海疆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绘航海图,后载入茅元仪《武备志》,标出了诸岛群的名称和位置。公元1512年,《广东通志》明确西沙﹑南沙群岛为中国海防区域。所以,南海是中国“历史水域”,其历史依据是再严格不过了
■如果中国对南海“历史水域”的主张依据一般国际法确立无疑,那么相关水域之内的岛屿礁石当然全属中国所有。至于建机场甚至部署一些必要的军事设施等,显然就是中国在自己疆界内的国内行动。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类言辞,别人不一定能体会其中含义。但如果将其中法理明确表达,能使别人引起共鸣的可能性将会大增
海牙临时仲裁庭对菲律宾有关南海争执控告中国一案,已经作出所谓裁决。根据相关报道,菲律宾“胜诉”是因为裁决书中严厉地宣称中国绝无“历史权利”,即认为中国主张的“九段线”毫无“法律依据”。
“历史权利”这一点,是菲律宾诉状中最实质也是最具要害的一点。因为菲律宾知道,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长达320条再外加9个附件,对于海事问题细节之规定以及海事争端如何和平解决等,有很详尽的规定,但也有若干相关事项并未涉及、亦无规定,“历史水域”即是一例。而中国对南海的声索,主要建立在“历史水域”原理之上。
菲律宾抓到这个漏洞,很有技巧地在这场争端仲裁中设下了一个陷阱。说这是一个陷阱,原因是菲律宾故意请求临时仲裁庭依据公约,来评判中国的历史水域,及因此而带来对其中岛屿礁石拥有权的主张和处理。换句话说,只要仲裁庭在公约中找不到有关“历史水域”的文字,它的结论就可说找不到“法律依据”。
可是,有辩才的人能够立即抓住其中的漏洞。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既然在这个公约里,找不出否定中国“历史水域”的文字规定,那么也就可以说,否定中国“历史水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既然如此,临时仲裁庭的最终答案,可以是正,也可以是反。至于最后的选择,就完全凭临时仲裁庭5个仲裁员的主观意愿了。这个情况,一定要正告全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公约的序言有明文告诫,即“本公约未予规定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所以,虽然公约对于中国“历史水域”的法律地位没有规定可循,但按照公约序言的告诫,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法(习惯国际法)”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可以找到支持中国声索的依据。当然,菲律宾方面是不希望临时仲裁庭注意到这点的。
此外,按照公约附件规定,临时仲裁庭的5个仲裁员中,争端双方各自从现存仲裁员名单中选一名(可以是本国人),其他3人则可由争端双方以协商方法选出,或者由争端双方转请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指派。问题在于,涉事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除了菲律宾选择的人选以外,全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指派,而这个庭长正好是个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仲裁结果能否维护公平正义,就可想而知了。
表面上看,菲律宾赢了。但这远远不是全部的真理。按照习惯国际法,中国绝对有法律依据可寻。
第一,习惯国际法(案例法)有承认“历史水域”的实例。譬如,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在挪威和英国有关渔业之争案例,以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有关大陆架案例中,即确认了“历史水域”的存在。
联合国的国际法委员会曾经解释,“历史水域”是基于历史而来,但要建立如此的权利,必须有严格的历史依据。中国在南海的历史依据,基于几个世纪的渊源。汉朝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设置珠崖﹑詹耳两郡,开始管理南海疆域。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对南海诸岛也有详细记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绘航海图,后载入茅元仪《武备志》,标出了诸岛群的名称和位置。公元1512年,《广东通志》明确西沙﹑南沙群岛为中国海防区域。1830年的《海防辑要》一书,将西沙群岛诸岛屿列为海防要地。所以,南海是中国“历史水域”,其历史依据是再严格不过了。
第二,习惯国际法中有一个“跨时间法”的原理,在“帕尔玛斯岛屿”一案中曾有过阐释——如果一个权益是建立于以前某个世纪(或时期),那么它的合法性即当用那个世纪(或时期)的国际法来衡量,而不可用若干时间后已改变的国际法来加以否定。
这对于中国“九段线”的法理基础,至为重要。因为“九段线”是中国于1947年划定的。那个时期的国际法并不排斥“历史水域”的观念,也没有别国提出异议。就连当时出版于美国且具有权威性的地图,也将南海按照“九段线”示意,注明属于“China(中国)”。
那么,面对所谓仲裁,中国如何回应而不失大国风范呢?对此,我们应该先有两点认识:一方面,如果中国对南海“历史水域”的主张依据一般国际法确立无疑,那么相关水域之内的岛屿礁石当然全属中国所有。至于建机场甚至部署一些必要的军事设施等,显然就是中国在自己疆界内的国内行动。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类言辞,別人不一定能体会其中含义。但如果将其中法理明确表达,能使別人引起共鸣的可能性将会大增。另一方面,在今日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冀以大国身份出现国际舞台,无疑应以凭专业追溯法理求证为上策。
基于此,再来看看中国反击的方法。按照公约附件有关规定,任何一方如对裁决之解释或执行有争端,首先可提请临时仲裁庭作出相应答案;如仍不满意,则可提交公约第287条所规定的另一法院或法庭处理,包括国际法院、按公约附件成立的国际海洋法庭等。即中方可保留以书面声明方式“选择”国际法院(或另一个机构),来解决解释和执行的争端。而按照公约附件规定,这个法院裁判将对中菲双方有“确定性和拘束力”。
这个办法有两个好处:一是中国可以得到翻案的机会;二是中国以讲法理的手段取得成功,在国际上可以受到更多的敬重与折服。
中国挽回所谓仲裁之不利,需要大智慧大勇气。我们更有必要以具体行动证明,中国具有比别人更能讲法理的大国风范。
(作者为美国纽约大学在职终身教授)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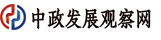 | 国际频道
| 国际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