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部中小城市发展,国家和省级政府应有一个长远和整体的考虑,要有一些特殊的扶持政策,保证这些城市能够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持一定的人口集聚,有一些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
智库观点
刘立峰
最近,笔者到西部几个地市调研,深切感受到除了与省会城市和少数大城市相邻区域外,其他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境遇不佳、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前景不明。这些城市地处内陆偏远地区,但是,仍然居住着大量人口,是区域发展的中心,联接着广大的农村,对政权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基础和保障性作用,因此,必须重视这些城市的未来发展。
存在的问题
一是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2017年,四川省会成都的首位度系数(区域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经济规模之比)高达6.7,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最高的,西部地区的银川、西宁、兰州、西安等城市的首位度系数也排名全国省会的前列。近些年,在四川省内,经济排名后几位的地市与成都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在持续拉大。与2010年相比,2017年,遂宁、广安、广元、雅安、巴中的GDP占成都的比例分别下降了0.8个、1.3个、0.6个、0.8个和0.8个百分点。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大城市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西部的资源和要素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挤占了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小城市更快走向衰落。
二是资本和人才大量流失。1.资本外流严重。目前,江浙一带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比大都高于80%,有些甚至高于100%。而2017年末,四川省的雅安、广元、达州、广安等地市的存贷比却分别只有54%、51%、41%和40%,有近一半的当地资金被转移到外地使用,造成了当地金融资源大量外流。2.人才不断流失。以四川剑阁县为例,2013—2017年,该县共招收硕士研究生和选调生95人,目前已有30人流失;2013年以来,县教育局以年均80人的规模公开招录,已聘教师每年却以15—20人的速度流出县外。大量教师和学生外流,带走了优质教育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在剑阁县内就读学生只有5万多人,但是,每年就有9000多人到绵阳、成都等相对发达城市就读。由于人才流失,目前,西部中小城市大多数企业人员文化水平偏低、技能单一,很难承担起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重任,又缺乏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高端产业很难发展起来。
三是产业创新发展缺乏支撑。突破原有的产业发展格局,实现转型和创新发展是西部中小城市崛起的关键因素。近十多年来,尽管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是,资源化、低端化仍是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广元市为例,2011年,煤炭、有色冶金等传统资源型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9.4%,到2017年,上述比例仍高达34.7%;2011年,广元装备和信息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值的14.3%,到2016年,这一比例反而下降到12.5%。目前,西部中小城市主导的工业品仍然是煤炭、电力、水泥、有色等资源型、高耗能产品,结构变动不大,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由于长期专注能源资源单一产业(单一企业),导致这些城市的产业体系不完善,产业不配套。招商引资难度非常大,“低端产业不想要、高端产业难引进”,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发展新兴产业的能力十分有限。
四是人口外流导致空心化。2017年,四川省只有成都、攀枝花少数几个地市人口净流入。其他地市州基本都是人口净流出,总数高达875万。广安、达州、宜宾外流人口超百万。沪州、达州、宜宾、资阳、广安外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5%。目前,中西部有些城市70%以上的青壮年在外打工,企业劳动力短缺和招工困难情况时有发生。农村人口流失现象更为严重,空心村成为普遍现象,新建的农业园区和农村新居平时大量空置,数万人口的乡镇,如果不是节日,街上鲜见行人。人口的流失意味着劳动力的流失,也意味着市场和消费规模萎缩,金融、物流、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很难有所发展,低端化现象严重,使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失去依托。西部许多中小城市都提出过建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城市的目标,但十几年过去了,城市人口基本持平甚至减少。
原因分析
西部中小城市逐步走向衰落有发展战略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还有交通方式改变的原因。
一是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产生虹吸效应。
无论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还是主体功能区战略,或是城镇化发展战略,都以强化核心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为主要方向,而与这些中心城市地理距离越远的中小城市,发展条件越差,机会越小,越来越被边缘化。这导致生产要素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偏远城市失去比较优势。例如,成都市将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确定为加快发展的产业,川菜产业园内的调味品企业受政府调控,不允许搬迁,其中的郫县豆瓣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允许转移。这让希望引进相关产业的中小城市失去了机会。
二是高铁等新兴交通方式改变了区域格局。西部中小城市大多位于大的经济区或都市圈的边缘地带,有些还是省际接合部的边缘区域,这些地区在空间上远离发达城市和省域政治经济中心,不能直接而有效地接受区域经济中心的辐射和带动,往往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属于“经济冷点”。高铁等快速交通方式一方面给这些城市带来了短暂的人流,但另一方面,跨城市通勤时间的大幅度压缩,也加剧了城市人口、购房、消费的外溢,造成中小城市越来越没有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城市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反而对中小城市的要素资源产生虹吸效应。
三是盲目的生态规划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西部中小城市大量向中央和省级政府申报各类生态保护规划。以剑阁县为例,就先后申报了四川剑门关国家森林公园、四川翠云廊古柏省级自然保护区、剑阁剑门关省级地质公园等项目,总面积占全县辖区面积的一半。雅安市也有同样情况,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占全市总面积的54%。保护区捆住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手脚,红线范围内的土地不能动,交通、产业项目不能布点,企业想进入也有了更高的环境容量限制。
四是生态补偿机制和资源本地化政策未落实。
西部中小城市大多位于生态功能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是,保护任务也异常繁重。尽管有中央转移支付,但是,涉及生态补偿的资金却很少。广元地处嘉陵江上游,国家有断面考核要求,但是,全年的保护资金却只有200万元,资金缺口巨大。从全国来看,除新安江流域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其他地区均没有成功案例。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本地化政策只在延安等极少数革命老区有所体现。
五是土地收益的地区差异造成发展差距扩大。
2017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万亿元,其中,北京、杭州、武汉、南京、上海、重庆、天津、成都8大城市合计就达1.4万亿元,占35%。排名前20位城市土地出让金合计超过了总额的一半,排在前50位的基本都是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西部中小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与东部城市、西部大城市根本无法相比,2017年,四川广元土地出让收入只有19亿元,仅相当于成都的1.6%。土地财政收入是城市政府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高低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能力和水平,也造成了城市间基础设施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对策建议
对西部中小城市发展,国家和省级政府应有一个长远和整体的考虑,要有一些特殊的扶持政策,保证这些城市能够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持一定的人口集聚,有一些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
第一,实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不少的西部中小城市位于革命老区,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规划布局和项目核准方面应尽量给予这些城市优惠;能够在老区中小城市落地加工的,有市场、有潜力的石油天然气炼化等深加工项目应尽可能在当地布局建设;在对口援建中,建立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机制,与东部沿海地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支持发展较好的中小城市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区。
第二,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国家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重点应向西部中小城市倾斜,加大纵向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参与和责任分担机制,共同推进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探索各方都能接受的实施方案。由住建部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牵头,对重点生态保护规划进行适当调整,根据生态保护的实际需要,保留核心区功能,缩小缓冲区和试验区范围,释放经济功能,为西部中小城市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
第三,引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大幅度减少对北京、上海等知名高校的中央财政拨款额,将其转移到西部中小城市,建设应用型大学或大专职业学校。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将西部中小城市义务教育教师和公立医院、乡村卫生院职工工资等事权和支出责任上划中央财政。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积极引导大城市优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在西部中小城市布局。
第四,给予当地政府更大的改革空间。对战略地位重要、人口密度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西部县可考虑升格为市。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土地管理权和收入支配权。允许农村整理后增加的建设用地留在乡镇调剂使用,或给予乡镇政府一定比例土地出让收入分成。允许农村宅基地部分转让给城镇居民,实现农村居民出宅基地,城镇居民出资金,共同建设新城镇的新局面。
第五,促进资金和资源分配的公平化。西部中小城市政府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必须充分考虑中央和省级公共资金的再分配问题,逐步解决这些城市投资不足的问题。省级层面的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决策要更多关注中小城市的利益,特别是边缘城市的诉求,注意征询这些城市的意见。西部省会城市往往一城独大,环境容量已经没有,产业也需要向外转移。应参照广东的做法,由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择优扶持中小城市产业转移园区建设,促进省会城市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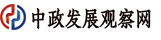 | 经济频道
| 经济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