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是对近年国内“科幻热”现状的描述。7月下旬的这个周末,因为大刘和郝景芳的出现,在“理想国”举办的“未来之近、现实之远”的活动现场被火焰般的炽烈包围。
2015年,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被称为“科幻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2016年,在大刘的推荐下,年轻的“80后”女作家郝景芳凭借作品《北京折叠》入围雨果奖。人们对科幻关注的热情蔓延到对郝景芳的好奇。因为过于低调,拒绝了大量采访,她被笼罩上更加神秘的面纱。
天体物理学、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人们评价她:白天是清华金融女,晚上是宇宙学女神。
针对一些传闻,郝景芳笑着回应:“我在国务院很小的一个研究机构工作,给政府写一些报告。我没有见过习大大。有人传我给李克强总理写信,这个事情已经被越传越远。是不是我接下来身份地位就到了随便进出中南海?”这位优秀的“别人家孩子”逐渐被神话。
故事接龙
集齐中国顶尖的科幻作家,是否可以召唤神龙?
2016年春节,一个关注未来与科技的媒体《不存在日报》举办了中国第一台科幻春晚。导演唐匪集齐了中国十二位顶尖科幻作家共同完成了一个以“节日”为主题的接龙故事。这其中,有刘慈欣,也有尚未得奖的郝景芳。
故事的开头,设置了一个外星观察员来到地球。接龙的规则是,每一位科幻作家,只能看到前一位作家留下的故事情节。设计这个接龙游戏前,导演唐匪颇费思量。刘慈欣该安排在哪个位置?他写的故事和情节发展,谁能接住?唐匪担心,身为中国科幻高峰的刘慈欣会将故事推向最大的高潮,也会带来接棒者的巨大写作困难。
最终,唐匪决定,把科幻圈内称为“姐姐”的郝景芳安排在了大刘的身后。郝景芳带着一贯的温柔甜笑,文字里有着对人类最大的善意。
“星际观察员G融入底层蓝星人中,以普通人的身份见证着蓝星文明的发展。不同于人类基于超自然信仰的节日,这个化身低级工人的特殊观察员所在意的‘节日’,都是关乎蓝星文明本质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节日’。”
大刘第9个出场。在他的故事里,人类放弃了探索太空的梦想,转而内向虚拟世界。互联网、移动互联、可穿戴设备、VR、物联网……人类争相上载自己,地球渐渐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后,现实中一个人都没有了,世界回到人类出现前的样子,森林和植被覆盖着一切,大群的野生动物在自由地漫游和飞翔……“只是在某个大陆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深深的地下室,其中运行着一台大电脑,电脑中生活着几百亿虚拟人类。”大刘将人脑与电脑直接连接的一天,称为“流产节”。大刘带着对人类外向探索与内向探索的担忧,写下了这个故事。
人类文明的进阶需要内向的和外向的两条路。郝景芳不仅成功地接下了这个故事,而且还和大刘抬了一杠。
在她的故事设计里,“流产节”被称为“脑域节”。 “脑域更新了有关神经网络的重要知识,现在整个地球联通为一个超级大脑,所缺的只是对外进发的动力。人类太沉溺脑域,几乎忘了宇宙。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让人类再度睁开看宇宙的眼睛。”
观察员G被女孩伊莲带到一处教堂。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外星人,伊莲射出无数根细小的箭头。在G的尸体向母星发出信号的几十年时间里,地球的超级大脑足够迎击战胜外星人,“这是千载难逢的唤醒意识的好时机。”
每一个科幻小说,都是作者价值观的表现。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天体物理学专业的郝景芳说:“天体物理学界认为,人类去外太空发展是非常不划算的,地球上的资源足够人类使用。只是一个如何治理的问题。”
“科幻春晚”2个月后,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入围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北京折叠》
暗黑的想法可以把某些人群永远藏在地下
2012年12月,郝景芳在她常去的水木社区科幻版发布了《北京折叠》这篇作品的初稿,并在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中连载完成。2014年于《文艺风赏》正式发表。
郝景芳并没对这部作品报以获奖的期盼。在她看来,一部小说写完后,它就是脱离了作者的存在,“它的命运与我无关,几乎没有一刻挂念它的死活。”直到它获了奖,郝景芳的感觉是:像是得知了某个在远方的游子的近况——原来你最近过得还不错。
在得知入围雨果奖后,她也只是在微博简单回应:“能入选雨果奖很惊喜。当初小说只发在一个新创的电子杂志上,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再次感谢宇昆兄的翻译。小说的翻译与被接受程度紧密相关。不能和大刘的作品一同入选,心中的遗憾甚至大过了惊喜。宇昆兄在帮助华人作品推广方面居功至伟。”
在此以前,《北京折叠》还受到了中国科幻坐标奖的青睐。在写获奖感言时,郝景芳正在计算明年财政收入预测,这是给全国人大的项目报告。彼时的郝景芳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下来,郝景芳突然有一种因为荒诞感而引起的伤感: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
郝景芳说:“我写作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自己的一些旁观目睹,那些画面和感慨存在心里太满,我需要一个载体将它们保存起来。”
曾经,郝景芳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小苍蝇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的家人孩子,听他们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忧伤困扰。她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和司机攀谈。司机讲起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排一夜的队,还未必能入园。
北京有重大活动,会采取一些限制措施,街道不再熙熙攘攘,而是变得整洁漂亮。郝景芳想:“有一些人是可以藏起来的,藏在看不见的空间。有了这个暗黑的想法,当然可以把某些人群永远藏在地下。”
由于读书时间很长,郝景芳的身边一直围绕各种喜欢谈论整个世界、感觉自己即将接管世界的跃跃欲试的学生,他们对未来充满奇异的期望。郝景芳在工作中,也会有机会参与一些会议,见到不少能够改变世界的大人物。
《北京折叠》里,郝景芳写的园子就是钓鱼台。所有的这些碎片在她头脑中碰撞起来,就成了《北京折叠》。“实际上我不认为它是一篇幻想小说,我写的也根本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郝景芳在“坐标奖”的获奖感言里写道。
《北京折叠》只是郝景芳设想的长篇的第一章,“只是看一下世界,并没有涉及改变世界。”但她迟迟没有动笔。一方面是工作太忙,写作计划太多;另一方面也是仍然在等待情绪的酝酿。
“这样一个有关不平等的故事,得到许多人认可,说明周遭世界的不平等如此昭然若揭。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邪恶,但一定意味着许多许多人生存的艰难。”郝景芳如此说。
学渣or学霸
她的预期可能是爱因斯坦的高度
郝景芳清华大学博士的高知背景,让很多人羡慕。网上一篇《白天是清华金融女,晚上是宇宙学女神,一枚清华“学渣”的逆袭史》的文章,在郝景芳获雨果奖提名后的几天内刷了屏。
2002年,郝景芳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她并不像新概念的大部分作家那样关注青春与疼痛,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科幻题材。曾有同学说,以为郝景芳会凭借着新概念作文一等奖的美誉保送到北大中文系,没想到她竟然考到了清华物理系。这就是大家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高中的时候,郝景芳就痴迷物理。海森堡、玻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普及版阐释,震撼了她的世界观;而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更让她叹为观止。“高三的时候我看科学和哲学,看爱因斯坦写的散文集,以及薛定谔写的宇宙真实性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关系的文章,我感觉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她曾经坚定的理想是做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她上了清华物理系,并读到了硕士研究生。
郝景芳不止一次谈到了焦虑。这份焦虑,在她进入清华读书后,陪伴了她一段时间。在这里,她发现清华的大牛太多了。曾经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找班里的大牛请教一道怎么都解不出的题,大牛看了一眼,实事求是地说:“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没做,你看看讲义吧。”
关于“成功”与“焦虑”,郝景芳曾经在短片小说集《去远方》中有过故事描述。在名为《癫狂者》的小说中,一位一直成绩优异的男主人公开始怀疑自己的成功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操纵和监视所得,因而陷入焦虑与癫狂。文中详细记录了心理咨询师的治疗过程。郝景芳说,对“焦虑”的思考,每个人都需要,“在写作前查了一些资料,有一段时间一直对心理问题感兴趣,对自己有自我分析跟自我疗愈的过程。”
这与个人对自我的预期相关。“预期的高度可能是爱因斯坦的高度”,达不到,就会陷入幻灭。
感到自己在天体物理学方面无法做出杰出成绩后,郝景芳改读宏观经济学的博士。这个改变,使她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多元,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建构她的科幻世界,建立运行规则。探讨人类的近未来,是郝景芳感兴趣的。比如,以人类科学技术及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背景,会发生什么?如果将商品经济无限放大,定价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一个人的价值是否完全被市场决定?是否完全被受众需求和数量决定?他的内里价值又是什么?
郝景芳上大学以后开始学大提琴,在科幻小说《弦歌》中,将天地为琴,以共振为歌,展开了一场对外星人的反击。
“我之前对我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给予了过多的重量,实际上是自我匮乏的一种表现。”郝景芳说,如今,她不再需要采访在座的每一个人才能确定自己好不好。“一个奖项也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太多不恰当的关注。”
“无类型文学”
脑洞大开,是科幻,也是寓言
郝景芳曾将自己的小说投给过主流文学杂志,但因类型不合适,收到过几次退稿。编辑告诉她,杂志不发表科幻作品。与此同时,同样的几篇小说也被科幻杂志退稿,理由是过于文学化,不太科幻。这是她在相当长时间里面临的尴尬。
高中时开始,郝景芳就特别喜欢看哲学家们写的关于人、自我、人类意识等这一类的书。关注宇宙、量子力学、人的自我意识,关注人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她很想写关于人和自我意识这样的书。
但是她的阅历让她无法书写。巨大的落差让她将目光转移到科幻。“我后来就从一些比较轻巧的、小的东西开始写,科幻里面假想一些东西,可能都不像文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后来慢慢加上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样就不是谈论一个终极命题,而是从生活中有小的困惑出发,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我确实想写的。”郝景芳在接受采访时说。
有些寓言化、模型化,郝景芳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更像是小寓言或者是小童话。“我自己写的东西,原来自己的定位是‘无类型’。既不是主流文学,纯文学,也不像科幻小说,脑子一动有一个闪念就写下来。”
虚拟空间自有虚拟世界的逻辑和战斗目标。而郝景芳的写作介于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它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郝景芳写作时会假想一个世界,然后去推理,她一定要把逻辑推通了,再往下写。
如果写人类,会以人类社会的一些内部运行规律为逻辑。在长篇小说《流浪苍穹》里,郝景芳设置了两个世界。假想了一个纯市场化的世界,政府的控制力量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另外一个世界是计划经济世界,与现实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知识创造性社会的计划经济,而非工业化。她的阐述,在晦涩与通俗易懂之间穿梭,就像她生于1984年的人生经历,前接计划经济,后连市场经济。
《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提名后,郝景芳和国内外的一些读者对这个小说进行过探讨。中国读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北京的特殊性等方面;美国的读者则更多地与她探讨自动化对人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动化不可避免,这些低水平的劳工该怎么安排?
“反映出你关注的内容与你生活的环境有关。”郝景芳说。
“社会制度的变迁”是郝景芳从小就感兴趣的。古今制度比较、中西制度比较、理论上跟现实的比较,郝景芳对这方面的兴趣已经有十多年。“看历史上一些制度演化变迁,中西思潮比较,看乌托邦等等。我是从小就对制度感兴趣,可能越到大学越感兴趣。最开始只是跟朋友思辨的乐趣,到后来喜欢去学那些课,读一些教材,看一些学者的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至于我确实是一直都对于制度比较感兴趣。”谈起社会制度,郝景芳来了兴致。
她喜欢假想一个类似于《镜花缘》的国家。“我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以后还会写别的制度,可能跟我们的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映照和联系。”郝景芳说。
 会员投稿
会员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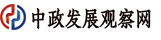 | 文化频道
| 文化频道




